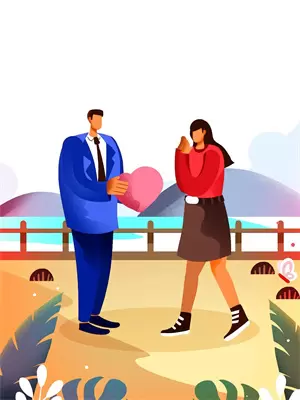
威士忌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滚落,洇湿吧台一小片深色木纹。劣质爵士乐在烟雾里黏腻地爬行,
隔壁桌醉汉含糊的叫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噪音。你指尖冰凉,捏着玻璃杯,指节用力到发白,
几乎要嵌进杯壁里。酒吧浑浊的暖光像一层陈年的油垢,黏在吧台冰凉的木面上。
威士忌辛辣的味道灼烧着喉咙,可怎么也烧不掉白天那根肥腻手指蹭过你腰侧留下的黏腻感。
你盯着杯底残留的琥珀色液体,
声音闷得像塞了团浸水的棉花:“那老东西的手…真想给他剁了。”醉酒后的你嗓音干涩,
带着酒精灼烧后的沙哑,视线落在杯底琥珀色液体晃荡的漩涡里,“今天简报室,门关着,
手又伸过来。真想把他指头一根根掰断。”旁边传来一声低沉的,带着胸腔共鸣的嗤笑。
Ghost 的存在本身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,即使坐在这最不起眼的角落,
紧绷的肩线也依旧蓄着豹子般的力量。黑色骷髅面罩遮住他大半张脸,只余下那双眼睛,
此刻在昏暗光线下,锐利褪去,漾开一丝极淡的,几乎称得上温柔的无奈。
他粗糙的指节碰了碰你紧攥杯子的手背,触感带着枪械摩擦留下的薄茧。“彼此彼此,
”他低沉的声音透过那标志性的骷髅面罩过滤,带着点沙哑的金属质感,
“我们那位‘将军’,满脑子只有怎么把边界线再往东推十公里。
天天琢磨着往火药桶里扔火柴,蠢货。” 他微微侧过头,面罩上那两个漆黑的眼孔转向你,
里面似乎藏着一丝疲惫的微光。他的声音低哑,像砂纸磨过木头,面罩随着话语轻微起伏,
“要不…别干了?” 酒精让这提议轻飘飘的,像一句梦呓。
他仰头灌下杯底最后一口龙舌兰,辛辣液体滑过喉咙的轨迹清晰可见,
空杯磕在吧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你嗤笑一声,指尖划过冰冷的杯壁:“好啊,
明天就递报告?” 你们对视着,谁也没有再说话,
只有酒吧里嘈杂的声浪填充着这短暂沉默的空隙。这念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小石子,
只激起一圈微不足道的涟漪,便沉入了现实的淤泥里。酒馆浑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。
这念头像水汽,在闷热的夏夜短暂升腾,又在黎明冰冷的现实里摔得粉碎。第二天酒店房间,
晨光刺眼。你沉默地套上战术腿套,冰凉的金属枪套贴上皮肤,激得你微微一颤。
身边床垫凹陷处还残留着他的体温和硝火混合的气息。他早已穿戴整齐,
幽灵般的骷髅面罩遮住所有表情,只在你起身时,俯下身。隔着那层象征死亡的黑色织物,
一个吻落在你额头,干燥、温热,带着弹药残留的硫磺味和皮革的冷硬气息。短暂得像幻觉。
门轻轻合拢,咔哒一声,隔绝了昨夜所有酒气和短暂逃离的幻梦。现实如冰冷的钢索,
重新勒紧心脏。“活着。” 这是他每次离开时的固定告别语。你含糊地应了一声,
鼻尖萦绕着他身上那股硝烟与皮革混合的味道,房门咔哒一声关上,带走了最后一点暖意。
战争爆发得毫无转圜。大国角力,庞然巨物轰然相撞,你们这些被精密打磨过的武器,
瞬间被推上最前端的锋刃。保护目标,政要,代号“基石”。你的职责,
是成为他最后、最坚硬的盾。情报冰冷刺骨:敌国最锋利的“矛”,
那支令人闻风丧胆的“141”特遣队,已潜入城市。矛尖所指,正是“基石”。
Ghost,简报上的名字像淬毒的冰锥,扎进你思维核心。短短几个月,
酒馆里那点微弱的暖意便彻底冻结在冰冷的瞄准镜视野里。高处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,
刮过裸露的皮肤。你像一块冰冷的岩石,紧紧贴着狙击步枪。透过高倍瞄准镜,
十字线稳定地套住下方严密戒备的政要车队。
目标车辆的车窗玻璃在光学镜片里呈现出特殊的、带着细微纹路的质感。废弃水处理厂,
巨大的混凝土结构在暮色中投下狰狞的阴影,如同巨兽的骸骨。
高塔锈蚀的钢铁骨架刺向铅灰色的天空。风在高处变得尖利,呼啸着穿过钢铁缝隙,
带来远处城市模糊的硝烟味。你伏在冰冷的水泥平台上,狙击步枪的金属托腮板紧贴着颧骨,
冰冷坚硬。心跳在死寂中擂鼓,每一次搏动都沉重地撞击着胸腔肋骨。瞄准镜的十字线,
如同命运冰冷的刻度,缓缓移动,
管道、巨大的沉淀池阴影、布满锈迹的阀门……搜索着那个唯一能穿透“基石”防御的威胁。
你的手指悬在冰冷的扳机护圈上,细微地颤抖。突然,瞄准镜的视野边缘,
对面那座更高、更孤绝的冷却塔顶端,一个极其微小、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反光点,
极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。像黑暗中悄然睁开的恶魔之眼。你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,
又在下一秒疯狂奔涌,冲向四肢百骸,带来一阵眩晕般的灼热。镜头猛地甩过去,
视野剧烈晃动、收缩、稳定。十字线中心,清晰地框住了一个身影。尽管隔着遥远的距离,
尽管那身影大半隐在阴影和伪装之中,但那种融入骨血的熟悉感,
像一道高压电流瞬间击穿了你所有的神经末梢。Ghost伏在冷却塔边缘的混凝土矮墙后,
姿态完美,与身下冰冷的灰色建筑融为一体,像一块沉默的岩石。
一支修长的狙击步枪稳稳架设。那身标志性的深灰色作战服,
以及……那覆盖了半张脸的、令人心悸的黑色骷髅面罩。
那个在无数个清晨给你留下冰冷又灼热印记的骷髅面罩。时间被无限拉长,又瞬间坍缩。
冰冷的金属扳机硌着你的食指指腹,寒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脏,几乎将它冻僵。瞄准镜里,
那个曾无数次拥抱你、吻过你、和你一起在肮脏小酒馆里咒骂命运的男人,
正用他黑洞洞的枪口,指向你此刻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目标。他的枪口,也等同于指向了你。
瞄准镜里,他微微调整了姿势,似乎在锁定目标。你的食指僵硬地搭在扳机上,
汗水瞬间浸湿了冰冷的金属,滑腻得几乎握不住。瞄准镜的十字线死死咬住他的头部轮廓,
那个戴着黑色骷髅面罩的头颅。喉咙里堵着一块烧红的铁,
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带着灼痛和铁锈味。早知如此……上一次他倾身吻来时,
就不该推开他抱怨他胡茬扎人。早知如此……在酒店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,
就该耗尽所有力气去纠缠,把每一秒都刻进骨头里。
早知如此……在第一次看清他面罩下那双疲惫却专注的眼睛时,
就该把那份压在抽屉最底层的退伍申请狠狠拍在长官的桌上……可惜,没有“早知如此”。
时间,空间,战场上所有的喧嚣和硝烟,甚至你自己的心跳和呼吸,
在那一刻被一只无形巨手狠狠抽走。世界化作一片绝对的、令人窒息的真空。
只有瞄准镜里那个身影,无比清晰,无比巨大,占据了你整个意识宇宙的中心。
对面钟楼高处,那个幽灵般的身影似乎也微微顿了一下。极短的瞬间,
你仿佛透过冰冷的瞄准镜,穿过遥远的距离,
捕捉到了他面罩眼孔深处一丝极其细微的弧度——那像是一个冻结在死亡边缘的笑。
你看到了他。他也看到了你。隔着数百米充满死亡气息的空气,隔着瞄准镜冰冷的镜片,
两道视线在虚空之中轰然对撞。没有惊讶,没有迟疑,
只有一种早已被命运书写完毕的、近乎残忍的平静。那平静之下,
是深不见底的、足以将灵魂都焚毁的痛楚。你看到他握着狙击枪的指关节,
因用力而泛出青白。然后,你看到了:就在那骷髅面罩上沿,靠近太阳穴的位置,
那唯一裸露的、一小片被黑色油彩覆盖的皮肤。他眼角的肌肉,极其细微地牵动了一下。
那细微的牵动,竟在瞄准镜无情的放大下,清晰地勾勒出一个……上扬的弧度。
一个在死亡阴影笼罩下,近乎温柔、近乎解脱的——笑意。那笑意像烧红的烙铁,
狠狠烫在你的视网膜上,烫进灵魂深处。你食指扣向扳机的瞬间,
握枪的肩部肌肉突然出现一个违反狙击手本能的微小后撤——那是只有你能读懂的肢体语言。
“砰——!”“咻——!”几乎在同一毫秒,你和他,隔着两个国家冰冷的距离,
隔着无法逾越的忠诚与使命,隔着所有未能出口的眷恋和悔恨,扣动了扳机。两个声音,
几乎不分先后,撕裂了高塔上死寂的空气。你指下的扳机,冰冷,沉重,却又轻得不可思议,
仿佛它自己挣脱了意志的束缚,完成了那早已注定的、机械的行程。
枪身在你肩窝处猛地向后一撞,巨大的后坐力震得你锁骨生疼,
世界在枪口喷出的炽热火焰和气浪中瞬间扭曲模糊。
.338拉普马格南弹以超高的初速离膛时,对面冷却塔同时爆出枪口焰。
0.92秒的飞行时间里,你看着自己射出的死亡精准扑向他的太阳穴,
而他的子弹却在计算好的提前量上诡异地向右偏移了22英寸,
带着亚音速弹特有的嘶鸣和高速旋转的灼热气流,几乎是贴着你耳廓的汗毛尖厉地掠过。
后坐力狠狠撞上肩窝的瞬间,沉闷的痛感扩散开来,你甚至来不及皱眉。
左耳畔的空气被极其尖锐地撕裂,一股灼热到足以烫伤灵魂的气流,如同情人最炽热的低语,
紧贴着你的耳廓皮肤狂暴地掠过。亚音速子弹特有的撕裂空气的嘶鸣声,
让你的左耳瞬间陷入一片死寂的嗡鸣。这失聪的空白,于你,
却像一声来自地狱最深处的、无比清晰的叹息,温柔得令人心碎。皮肤瞬间被烧灼起泡,
留下火辣辣的剧痛。巨大的冲击波狠狠灌入耳道,瞬间剥夺了你左耳所有的听觉。
世界被硬生生劈成两半,一半是尖锐刺耳、永无止境的嗡鸣,
另一半是诡异的、令人心慌的死寂。那片死寂里,
只剩下你右耳听到的、自己血液在血管里疯狂奔流的轰鸣。还有,灵魂深处某个地方,
彻底碎裂崩塌的巨响。时间被无限拉长、凝固。你的子弹没有空白。
它带着你所有的绝望和决绝,精准地、残酷地,
吻上了对面钟楼高处那个戴着骷髅面罩的头颅。你清晰地看到,自己射出的那颗子弹,
带着你全部的生命、全部的爱与绝望,旋转着,撕裂空气,划出一道笔直得近乎冷酷的轨迹。
它精准地钻进了瞄准镜视野中心,那张黑色骷髅面罩下太阳穴的位置。
瞄准镜剧烈地晃动了一下。视野里,那顶着的黑色骷髅面罩猛地向后一震,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