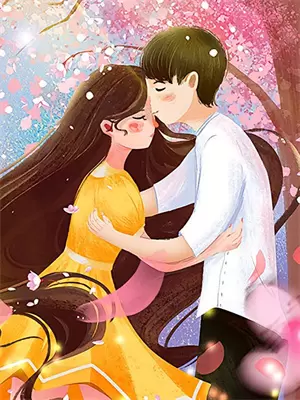小镇不大,人口不过千余,却藏着不少老故事,其中最出名的,便是关于一座古宅的传闻。
那宅子名叫“灯笼居”,坐落在镇子东头,紧挨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清河。
宅子不大,却气派非凡,青砖黛瓦,飞檐翘角,门前一棵老槐树已有百年历史,树干粗得两人合抱不拢,枝丫扭曲如龙,张牙舞爪地在风中摇曳,投下斑驳的阴影。
灯笼居虽保存完好,却无人敢住。
门窗常年紧闭,院子里野草疯长,墙角爬满青苔,屋檐下蛛网密布,风一吹便轻轻颤动,像在低语什么。
镇上的人说,这宅子闹鬼,尤其是每逢月圆之夜,远远就能瞧见院子里亮起一盏红灯笼。
那灯笼不大,红得刺眼,像一团跳动的火焰,摇摇晃晃地在半空飘着,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提着它在巡夜。
有人说,那是鬼魂在提灯游荡;也有人说,那是宅子里藏着的秘密在召唤过路人;还有人低声耳语,说灯笼的光能勾魂,谁盯着看久了,就会被拖进另一个世界。
关于灯笼居的传说,镇上流传了上百年,却没人说得清来龙去脉。
年长的说,那宅子原是清朝一位富商的别院,富商全家一夜之间失踪,只剩宅子空荡荡地立着,门前槐树下还留着一只翻倒的木盆,像被匆匆丢弃;爱讲故事的则添油加醋,说宅子里住过一个画师,画了一幅仕女图,画中女子夜夜从画里走出来,提着灯笼在院中徘徊,寻找丢失的魂魄;还有些胆大的年轻人信誓旦旦,说宅子里埋着宝藏,谁能解开灯笼的秘密,就能富甲一方,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,灯笼下藏着一只金盒,里面装着富商留下的遗书和珠宝。
这些传闻虽离奇,却没几个人敢去验证。
镇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:路过灯笼居时,得绕着走,尤其是晚上,谁也不敢多看一眼。
偶尔有孩子淘气,跑到宅子附近扔石头,大人总会急匆匆地跑来拉走,低声呵斥:“别惹那东西!”可就在那个炎热的夏天,一个外乡人的到来,打破了小镇的平静,也掀开了灯笼居百年未解的谜团。
第二章:林泽的到来那年夏天,清河镇来了个年轻人,名叫林泽。
他背着个旧书包,书包边角磨得发白,露出几根线头,穿着一身洗得褪色的蓝布衣,脚上蹬着一双布鞋,鞋底薄得能看见脚趾的轮廓。
林泽二十出头,模样清秀,眉眼间透着一股书生气,嘴角常挂着笑,看起来很好相处。
他自称是个写书的,专门跑遍各地收集奇闻异事,听说灯笼居的传闻后,特意从几百里外的省城赶来,风尘仆仆,满脸倦容却掩不住眼里的兴奋。
林泽在镇上唯一的茶肆“清风阁”住了下来。
茶肆不大,两层木楼,楼下摆着几张方桌,桌面上刻满岁月的划痕,楼上是几间简陋的客房,木板床吱吱作响。
老板娘翠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,圆脸红唇,嗓门洪亮,腰间系着一条灰布围裙,手脚麻利。
她见林泽模样俊秀,又斯文有礼,便多聊了几句:“小兄弟,你打哪儿来?瞧你这身打扮,不像是本地人。”
林泽放下书包,擦了把汗,笑着说:“翠娘,我是从省城来的,写书的,喜欢到处跑。
这次听说你们镇上有座灯笼居,故事多,就来瞧瞧。”
他的声音温和,像夏天的微风,带着点倦意却不失热情。
翠娘一听“灯笼居”三个字,脸色微变。
她端了碗茶递给他,低声说:“小兄弟,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你真要去?”她顿了顿,眼神里多了几分担忧,像在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。
林泽接过茶,喝了一口,清冽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,他咧嘴笑:“不瞒您说,我这人好奇心重,不亲眼看看,心里不踏实。
我不信鬼神,只信故事。”
他拍了拍书包,里面隐约露出笔记本的边角,像个宝贝。
翠娘叹了口气,压低声音说:“十多年前,也有个外地来的木匠,跟你似的胆大,非要去灯笼居瞧瞧。
结果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躺在河边,嘴里全是泥巴,疯疯癫癫地喊着‘灯笼、灯笼’,没几天就死了。
还有个卖货郎,夜里路过那儿,说看见灯笼飘在河面上,第二天就发高烧,烧得人事不省。
你可得想清楚喽。”
林泽听了这话,非但没害怕,反而眼睛一亮。
他从书包里掏出个笔记本,翻开一页,掏出根短得只剩半截的铅笔,飞快地记下翠娘的话,还笑着说:“这故事好,有嚼头。
翠娘,您还知道什么?多讲点,我记着。”
他的字迹歪歪扭扭,写得飞快,像怕漏掉一个字。
翠娘见他这模样,劝不动,只好摇摇头:“随你吧,别怪我没提醒你。”
她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,嘴里嘀咕:“现在的年轻人,真是不要命。”
林泽坐在茶肆角落,低头翻着笔记本,嘴角微微上扬。
他已经打定主意,要把灯笼居的秘密挖出来,哪怕只是个故事,也值了。
第三章:初探古宅林泽在清河镇住了几天,天天在茶肆里缠着老人们讲灯笼居的故事。
他记性好,手也快,一个个传闻被他写在本子上,密密麻麻地填了好几页,连纸边都被铅笔划得发黑。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,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去灯笼居探个究竟。
那天太阳刚落山,天边还残留着一抹红霞,河面上雾气渐浓,湿漉漉地贴着地面,像一层薄纱。
灯笼居在暮色中显得更加阴森,宅子周围的柳树低垂着,像在低声哭泣。
林泽背着书包,手里拿着手电筒,独自走向宅子。
走到门口时,他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,树上停满了乌鸦,黑压压一片,齐刷刷地盯着他,偶尔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叫声,像在警告他什么。
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相机,心里给自己打气:“不就是个宅子吗,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他深吸一口气,推开了大门。
门轴锈得厉害,发出一声长长的“吱呀”声,像极了人的低吟,刺耳得让人头皮发紧。
院子里杂草丛生,石板路上爬满青苔,走上去滑腻腻的,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,夹杂着腐木的气息。
宅子的正厅大门半掩着,里面黑漆漆的,看不清模样,像一张张开的嘴等着吞人。
林泽打着手电筒走了进去,光柱扫过墙角,几只老鼠受惊窜过,发出细碎的响声,墙上剥落的灰皮簌簌掉落。
正厅里空荡荡的,只有一张供桌孤零零地立在中央,桌面布满灰尘,上面摆着一盏红灯笼。
灯笼不大,纸面有些破旧,但颜色鲜艳,红得刺眼,像刚涂过朱砂。
林泽愣了一下,心想:“这宅子荒废这么多年,灯笼怎么一点不旧?”他走上前,伸手想摸摸那灯笼,手指刚碰到纸面,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,轻得像是风吹过草丛,又像是裙摆拖地的窸窣声。
他猛地回头,手电筒四处乱晃,光柱扫过空荡荡的厅堂,却什么也没看见,只有影子被拉得老长,像个扭曲的怪物。
“谁?”林泽喊了一声,声音在空荡荡的厅堂里回荡,带起一阵回音,嗡嗡地撞在墙上。
没人回答,窗外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,像在低声呢喃。
他定了定神,觉得自己可能是听错了,便继续打量那盏灯笼。
灯笼里没有蜡烛,空荡荡的,可影子在地上却晃动着,像是有光在里面摇曳,诡异得让人心跳加速。
他皱着眉,掏出相机想拍张照,刚举起相机,就听到耳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,低低的,像在耳语:“你不该来。”
林泽吓得手一抖,手电筒差点掉在地上,光柱乱晃,照得厅堂明暗不定。
他猛地转身,身后还是空无一人,只有风从破窗里钻进来,吹得他的衣角微微摆动。
他咽了口唾沫,强撑着镇定:“谁在说话?别装神弄鬼!”他的声音有些发颤,却透着一股倔强。
声音没有再响起,可空气里似乎多了一股淡淡的香气,像茉莉花,又像檀香,幽幽地钻进鼻子里,甜得让人头晕。
他皱着眉,觉得这地方太邪乎,决定先离开再说。
刚走到院子中央,他回头一看,那盏红灯笼不知何时已经亮了起来,红光幽幽地映在墙上,像一摊血,映得老槐树的影子扭曲得更加狰狞。
林泽头皮发麻,快步跑出了宅子,双腿发软,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回了清风阁。
回到房间时,他脸色苍白,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,黏在身上冷冰冰的。
翠娘正在柜台后算账,见他这副模样,忙放下算盘跑过来:“怎么了?是不是撞见什么了?”林泽喘着气,半天才挤出一句话:“那灯笼……真的会亮。”
他的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,手指还攥着手电筒,指节发白。
翠娘倒吸一口凉气,低声说:“我就说那地方不干净,你偏要去。
现在信了吧?”林泽苦笑,低头看看湿透的衣服:“信了,可我还是得弄明白。”
第四章:镇上的秘密与暗探林泽的经历很快传遍了清河镇,有人嘲笑他是自己吓自己,有人却开始议论纷纷,说灯笼居的鬼魂又开始作祟了。
第二天一早,茶肆里挤满了人,都来看这个胆大的外乡人。
林泽却没被吓退,反而更坚定了要查清真相的决心。
他坐在茶肆角落,翻开笔记本,把昨晚的见闻一字不落地记下来,字迹潦草却工整,连那股香气和灯笼的光都写得详细。
翠娘端了碗热茶给他,低声说:“小兄弟,我劝你一句,别再去了。
那宅子不干净,多少人栽过跟头。”
她顿了顿,压低声音:“昨晚我做梦,梦见个白衣女子站在我床边,手里提着红灯笼,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我,吓得我一身冷汗。”
林泽抬头笑了笑:“翠娘,谢谢你关心。
可我这人就这样,越是怪事,越想弄明白。
我不信鬼,我只信有故事没讲完。”
他喝了口茶,暖意顺着喉咙下去,脸色缓和了些。
翠娘见他执拗,也不好再劝,只叹了口气,走开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,林泽开始挨家挨户打听灯笼居的往事。
他敲开每户人家的门,笑容满面地问:“大爷大娘,知道灯笼居的事吗?”镇上的人大多不愿多提,要么敷衍几句“不知道”,要么干脆摆手让他走。
有人甚至关门时嘀咕:“这小子不要命了。”
直到他找到一个独居的老婆婆,才终于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。
老婆婆姓张,今年快九十了,眼神浑浊,背驼得像个虾米,走路颤颤巍巍。
她住在镇子边上,一间破旧的土屋里,门口堆着些潮湿的柴火,屋里一股霉味。
她见林泽上门,也不惊讶,只是慢悠悠地招呼他坐下,又颤巍巍地端了碗水给他,水面上漂着几片茶叶。
“张婆婆,我听说您知道灯笼居的事,能不能讲讲?”林泽开门见山,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。